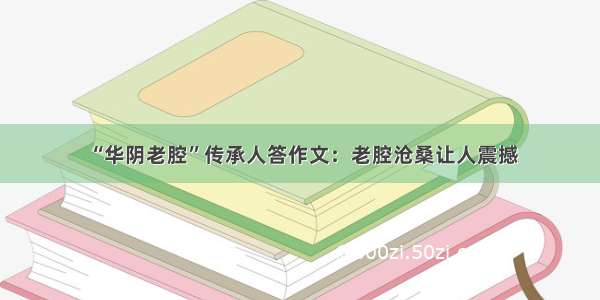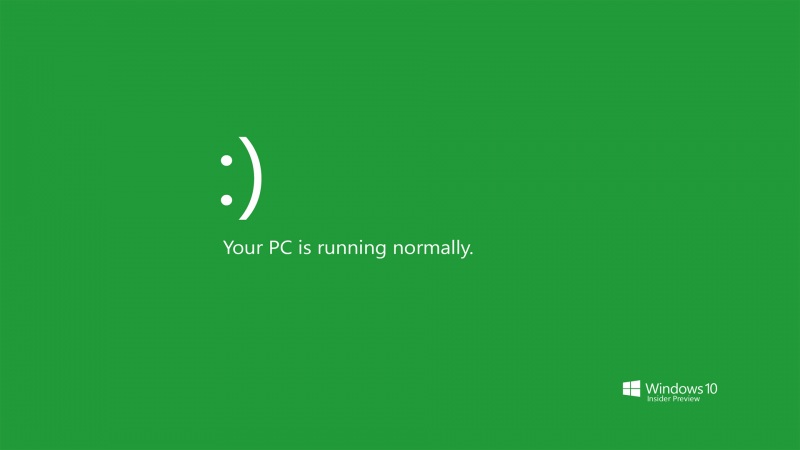▲
作家专栏栏
华阴老腔
文/刘成章
一声长吼回荡在天际。
久久回荡。
你来不及细听也无须听清那长吼源自哪里其中含着些什么字词什么意思,只知道是被一种陌生一种新鲜一种苍苍凉凉紧紧地攫住了,并且隐约感到在它的下边,似有沟壑纵横,华山高耸,黄水流,渭水洛水也在流。
忽然大幕拉开。皱折横亘的黄土高原。高原布景的前面,是一些农家常用的木制条凳。而一帮对襟短打的朴实农民从幕后走出来,手持各种自制乐器,或者拿了大老碗旱烟袋或线拐子,各自入座。
那是一双双常摸铣把车辕和粗麻绳的手。
乐器奏响了。一派阳刚之气一阵紧一阵慢一阵激浪四溅。那敲锣的虽然只拿着一只锣槌,却同时敲着大锣小锣,手若翻花。当他敲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就脱了外衫裸出双膀,只留个两侧开口的白粗布汗褂遮着前胸后背。接着外衫一摔,啐涎掌心搓搓手,就像要去掏粪或去铲土,但不是;他又以槌击锣,让锣声再次汇入雄壮的音乐音调掀起了美丽的波涛。
这时候,你不能不想起千多年前的《击壤歌》。哦,就是它,在眼前,在这现代化的舞台上,发出了灼人逼人的遗响。原始,朴拙,自然。它是如此奇特如此泾渭分明地有别于种种时尚表演,宛若野性的天籁,让人震撼,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剧场里爆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再看时,已是白眉白发被称做白毛的老农坐在台前。他手抱六角月琴,弹、唱、说、念,一人为之。那月琴已不知是何年做的,弹了多少遍了,几条紧绷的弦下尽是手指弹下的印痕,印痕连成一片。虽然粗糙而陈旧,但恍惚间,它却像真正的月亮一般,抱在白毛的怀里。啊,不!白毛其实这时候他整个的人就是一轮最美丽的月亮了,闪射着月亮的光,发出月亮的响声,而满台的星星都拱围着他,每件乐器每个声音都跟着他跌宕起伏跟着他闪闪发亮。
其实他这时候也不是月亮般地唱,而是在吼,是由脑后发出口腔大张的高八度的吼。发达的嗓子发达的野性基因。他的吼声高亢,峻拔,激越,苍凉,如一只强悍的鹰,总是盘旋在云际天际,而乐器的相对柔美的伴奏,却如滚在三条河里的流水,铃声叮泠,总是贴着地面游走。
是天和地的壮阔合作。
是的,高天是声水是琴。
那演唱其实是七分说唱,三分舞蹈。他们不时挥臂,呼喊,不时摆动身子。而唱到了情不可抑时,便如风雨的卷来,一起跺起了双脚。
天苍苍何其高也,路漫漫何其远也,那是一种人类心魄的高度和广度,而走在这样的路上,他们的脚下踩出了多么宏放的音响咚咚咚咚!
接着,月琴又抱在嗓音稍有嘶哑却又震摄人心的张喜民的手中。他留着分头的头发,仿佛总是被催动着汉时漕运风帆的风儿呼撩撩吹起,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农民。老腔原本是他家世代传下来的家族戏。他弹唱得从容而又自信。
他的周围,一派关中普通村庄里的日常图景:吃饭的吃饭,抽烟的抽烟,拐线的拐线,奏乐的奏乐,唱的唱。
他吼得万籁俱寂。他的吼声里有历史和黄土的颗粒:“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渠豁成黄河。”“一声军令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 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任何雕饰,只是生命的本真生命的赤裸裸的自然呈现,却散发着醉倒人的艺术魅力。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挫折牺牲,男欢女爱,浪漫的和现实的,快意的和悲壮的,粗砺的和绵软的,都在他的演唱里闪着异彩,成为对一个民族文明史的艺术追忆。一辈辈祖先的可亲影子,就在那追忆中闪闪烁烁。
也唱苦难也唱悲凉,凄切苦音在女声中撕裂着人们的心肺。但是正是这样的唱,千百年来,又总是激发出男子汉独对八荒永不退缩永不绝望的豪迈气慨。
舞榭歌台。金戈铁马。三国周郎赤壁。“催开青鬃马,豪杰敢当先!”喇叭高奏状出战马的长嘶,而歌声不止。到了激昂处,一人唱,满台吼,马鸣风啸,刀光剑影,时或四顾茫然。但是谁说雪拥蓝关马不前?看一个干瘦老汉冲出来了,他手里拿着长凳和木块,敲敲打打,忽而将条凳放平敲,忽而斜扶着条凳敲,不断变换着姿态敲,接着进一步高高抡起握着木块的手臂,用了全身的力气, 啪啪啪啪,将条凳敲打成英雄史诗大奇大美。同时歌声更酣,乐手们一齐帮腔。胸前狮子扣,哈!腰中挎龙泉,哈!好男儿,哪一个不敢冒险犯难!哈!啪啪!
啊,多么带劲多么震撼心灵的华阴老腔!
你不能不在心窝里发出阵阵回响。
那其实是山河的宏大律动。
它对于那些灯红酒绿下的阴盛阳衰或不男不女的浮糜灵肉,也许是一种提醒和救赎。
望台上。
干瘦老汉在敲打一阵之后,依然像平日劳动那样, 啐涎掌心搓搓手, 重新开始,掀起新的高潮。他敲打得那么认真,好像要从条凳中敲打出一个什么秘密来。
像节日的焰火灿烂着天地,像声声炸雷翻滚在山坡,回看张喜民,他演唱得何其精彩!演唱到每节结尾的时候,众声一齐掺和进来,而张喜民那常常高扬在云天里的吼声,早在人们不注意间,了无痕迹地款款落下,与伴奏与众声浑为一体唱成了拖腔,其声一改先前的豪放之气,已然变得出奇地婉约细柔,有如一条放生于水中的细长黄鳝,情意绵绵明澈透亮地左游右游,拐了好几道弯儿,让你舒服得受活得心尖儿都在打颤。而就是在这时候,却又有长板凳和喇叭的猝然切入,猛敲狂奏,并且众声齐吼,众脚齐跺,音乐则上下大跳。这一切都抽扯着你撞击着你爽意着你,使你觉得自己快要消融快要粉身碎骨了!
而啐涎掌心搓搓手, 众乐手依然不依不饶,光华追逼,高潮迭起,只见张喜民手中的月琴漫天挥扫,并且又掺和上一些人的拍手和吹口哨,满台子无人不动,无头不动,无臂无动,无腿不动,无颜不动,无声不动,动成生命的万类蓬勃,凤舞龙吟,长城内外战马奔腾,大河上下箭簇翻飞,交错碰撞又淋淋漓漓,而每个演出者都是一个炸药包了,让人怯于正眼直视,因为你只要稍稍扫一眼他们就会爆炸,但是还是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爆炸,冲击波冲向四面八方,那磅礴的气势排山倒海的力量,一霎时,有如从宇宙间的一个什么地方卷来一股威力无比的百万级飓风,把整个世界都给抬起来了!啊,这华阴老腔!
忽然疾捂钹弦。演出嘎然而止。这时候,观众们才从天翻地覆中清醒过来,多么兴奋!都转过脸去互相兴奋难捺地看看,赞叹不已,然后,又齐刷刷地把目光再次投到台上。
那是一群经历了无数沧桑的拉船人的后代。那是一群惯于吞咽油泼辣子彪彪面的汉子。那是一群民间古老艺术的传承者。他们所展现出的生命力是那么绚烂和昂扬!
与其说他们愉悦了观众的精神,毋宁说他们是给当今这浮躁世界浮躁生活,送来一股返璞归真的清新之风。
这样想时,却见演唱者一齐走到台边。
就像刚刚割麦回来,手执乐器的他们,那些老农、中年汉子和婆娘小伙,一个个额头汗珠晶莹。他们向观众们频频致意。
掌声如三水汇合,澎湃不息。
了答谢观众,又是一声长长的呐喊,雄豪,苍劲,悲凉。
那声音,仿佛从秦从汉一直呐喊到今天。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羊肚子手巾
记忆深处的陕北农民,不论是老汉还是青年,几乎人人都会有一条毛巾。陕北盛产山羊绵羊,人们常吃羊肉,表面布满绒毛的毛巾就像羊肚子(羊胃),所以我们陕北人都把毛巾称为羊肚子手巾。不过那时候的人们不是拿它洗脸——洗脸用一块破布就行了,而是把它当御寒、遮阳、挡尘的帽子用。
每当吃了早饭,汉子们去上地的时候,都是顺手从墙上或炕头拿了羊肚子手巾,往头上一扎,然后扛犁,牵牛,甩鞭子,走进一天的辛劳。羊肚子手巾是明度最强的颜色,汉子们在暮色四合中踽踽走回,婆姨们也许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却能从那远远晃来的一点白中,感知他们饿了的模样,于是赶紧往灶膛添柴。转脸便见汉子们已到了窑门口,用羊肚子手巾拍打着肩上腿上的泥土草屑,然后进门脱鞋上炕,顺手把羊肚子手巾放在哪儿,自在地等着即将端上的酸菜洋芋小米饭。羊肚子手巾好像一首绝美的小诗,年年月月,点缀着他们的“日出而作”和“日入而息”。
其实羊肚子手巾也点缀着苍莽的陕北高原。陕北高原少雨少河流,更距大海很远很远,但连绵起伏的山峦就像一望无际的滚滚波涛,而山野间处处晃动的羊肚子手巾,就像片片白帆。碰上天就要下雨,滚滚黑云仿佛要压到地上,在一片迷茫混沌之中,天上忽然划过一道闪电,这时候你看吧,这儿那儿,或者背着柴,或者挑着粪,或者开着手扶拖拉机的陕北庄稼汉,他们的头上,就像闪耀着一段一段的小小闪电。若是逢集,眼前便成了羊肚子手巾的世界,白花花一片躁动喧嚣。
陕北是闯王李自成的家乡。遥想当年李自成率众出征的时候,那些衮衮勇士的头上,只能是裹着家织的粗布方巾。那么,我想问,以羊肚子手巾取代粗布方巾,始于何时?是谁第一个把它扎在头上?群山默默,无人可以说清。但是起码可以说,机器的轰响应该是它的源头,羊肚子手巾应是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出现之后的产物。可以想象,羊肚子手巾问世之后,就逐渐有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色品种,其中不乏阔人使用的奢侈极品。但贫穷的陕北汉子购买力是极为低下的,他们使用的羊肚子手巾上绝无什么繁复的图案,只是两端各印有两三根或蓝或红的彩色线条,略加装饰。其实,那白底上的几根异样的线条,浮漾在满目荒烟蔓草的情境里边,就足够销魂的了,其中每一根都像不曾被污染过的倒映着野花的小河,流淌在历史的大野间。
羊肚子手巾是有味道的:风的味道,雨的味道,太阳的味道,男子汉的味道,渴望着过好日子的味道,广交朋友和攻难克险的味道。戴着它,即使在大旱之年,人,人的头上,总是充盈着湿淋淋的雨雾,仿佛近谷谷绿,近豆豆嫩,它美得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白色的雄性的牡丹。哦,令人眼馋令人迷醉的羊肚子手巾!
而生来就是光着脑袋的娃娃们,已经八九岁了,十二三了,还是光着脑袋,这时候就往往由不得要向大人的头上瞅瞅,眼神里充满了艳羡之光。大人便笑眯眯地捏一下他的小脸蛋:“娃呀!你才多高!急个甚!好生长吧,一棵草终究要开一朵小白花哩!”当娃娃们确信自己已接近于成为后生的时候,大人们也几乎在同时默认了这一事实,就把用旧了的羊肚子手巾给儿子郑重地往头上扎去,这时候茫茫环宇的纷繁风景中,一定有左近的树的舞蹈,河的歌唱,这几乎等于在举行一场极富文化意味的陕北式成人礼了。这时,娃娃的膝上也许还有恶作剧落下的擦伤,但他心上已是青葱一片。过不了多久,当他们自己的手中有了几个钱的时候,就想买一条崭新的羊肚子手巾;而一旦买来扎在头上,地上就多了一团雪,天上多了一朵云。以后的日子,他常常要把那羊肚子手巾放在河水里,揉揉搓搓,让那白雪白云益发鲜亮。当小伙子每天出门的时候,那薄薄的雪团云朵,就任由他拽着两端,任由他先裹住脑后,然后流畅地在额前绕着花子,最终打成一个漂亮的英雄结。英雄结所强化和突显的,是陕北后生的帅气和悍勇。
广袤苍凉的陕北是爱情的浪漫沃土,那些曾经热恋过的青年男女现在也许老去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信天游却记下了他们动人的镜头:“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咱招一招手。”而在招手的时候,为了把一肚子的情意都表达出来,小伙子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从头上摘下羊肚子手巾,久久地挥在手中,那羊肚子手巾上的情意的光波,一圈又一圈地在山间播散。而当有一天情人们近距离相会的时候,那羊肚子手巾一般绝不空着,里头或者包着一把酸枣、一块冰糖,或者一颗木瓜(陕北所谓的木瓜,其实指的是文冠果)、一颗香瓜,甚或,里头会是一层一层的纸,纸里拿出来的竟是一只从街上买来的卤猪蹄蹄。这看起来虽然没有现在的新潮青年手捧一束鲜花那般高雅,但那爱情的纯与真,却是惊天地泣鬼神旷世少见:“只要和妹妹配对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
然而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陕北汉子更多的还要为生计操劳不息,所以羊肚子手巾除了有浪漫的一面,还常常浸透着劳作的艰辛。人们总能看到,在锄地的山上或砍柴的崖边,疲惫的汉子们常从头上解下羊肚子手巾,去擦掉脸上膀上滚滚欲落的汗水,拧干了汗水再来擦。寒冬的西北风放肆嘶吼的时候,连泥土都能冻成石头,但它吹到羊肚子手巾上边,冷便被滤掉大半,那风到脖子,到脚尖,到全身,几乎没有丁点的冷意了。要是哪天干活时受了伤,羊肚子手巾又成了包扎带。
他们一生总会用上十条八条的羊肚子手巾,每一条都会紧贴着他们的发肤,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笑,直到白生生的颜色变黄了,变褐了,也烂了,用它补了袜子或纳了鞋底。最后,在某一个多云的早晨或某一个霞光四射的傍晚,它终于成了细碎的粉末,与敦厚无垠的黄土地融为一体,黄土地终于又增加了些许营养五谷和草木的物质。
我虽然自小生活在陕北的城市,但因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秧歌队的成员,甚至担任过秧歌队的伞头,所以在我的头上,也无数次地被羊肚子手巾艺术过,生动过。每到那时候,我就感到自己跨入了另一种境界,甚至感到自己就代表了淳朴勤劳善良。我初中毕业时曾经到照相馆照过一张半身相,主要装饰品就是脖子里的一条羊肚子手巾。好多年之后,北京知青来陕北插队,我曾见他们中有人头上扎起了羊肚子手巾,甚为激动,因而写了一首诗,被人谱曲传唱。
大概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回到延安,蓦然发现我的农民乡亲们头上的羊肚子手巾,那栖息了二三百年的白鹤,徒留鸣声,一夜之间全都飞得无影无踪了。后来经过深入探访,发现那些白鹤并未远离,其数量和种类反而更多了,只是都在人们家中筑了巢,巢在洗脸架上、枕头套上。我同时发现陕北农村有了大鬓角和休闲帽,有了丰富的五颜六色。对此,我感到高兴,又有些失落,心情复杂。时代的恢弘大书上,陕北曾经拥有的一页韵味深长的文化图景,是无可挽回地翻过去了。
好在与此相伴的是文艺舞台的空前活跃,羊肚子手巾以更阔的领域和更强的亮度出现在了世人的视野中。龙腾虎跃的安塞腰鼓,如泣如诉的陕北民歌,众多的电视剧,频频举办的美术展览,到处都能看到或感受到头扎羊肚子手巾的后生的影子。它们鲜活依旧,美丽依旧,气韵依旧,神采依旧。我百听不厌的信天游还是那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每当歌手一张嘴,我就感觉地上仿佛突然裂开了个泉眼,一股白色的水柱喷射而上,直冲蓝天,久久地摩挲着云彩,使得云彩也在抖动。我心里明白,歌手一次次唱出来的“羊肚子手巾”,其实只是几个普通的字啊,但此刻,它以一种满含陕北黄土香和糜谷香的亲切意象,展示着它的无穷魅力,其旋律仿佛充满了我们神州大地的整个天空,荡气回肠。我便想:羊肚子手巾,你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历史符号了,你将永远存留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中。
《光明日报》( 10月16日15版)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