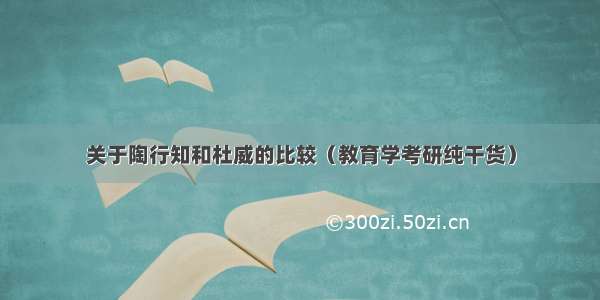作者简介:储朝晖,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始于19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陶行知逝世杜威发来唁电。陶行知从杜威那里获得思想和理论启发,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创建晓庄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创新。全方位、多视角考察和辨析显示,杜威与陶行知在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关系是原理与应用。杜威对陶行知思想和事业的影响都是关键性的,没有杜威来华,陶行知和杜威其他中国学生的人生将有所不同。他们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与激励,成为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价值取向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共同体,大大增强了中国教育的现代性,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关 键 词:杜威;陶行知;投射效应
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02-0076-15
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陶行知的关系论述已经很多,也比较模式化。消除各种主观因素干扰,探究客观原本的杜威对陶行知影响的真实状况,仍有较大的空间。
一、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
理清杜威对于陶行知影响的基础是明确陶行知与杜威的交往过程。现在发现陶行知与杜威的直接交往起点在哥伦比亚大学。
杜威是190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任教,直到1930年,他的思想影响在美国1905年就达到一次峰值;陶行知是19秋天从伊利诺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直到198月离开美国回国。
在这期间陶行知与杜威有多少交往依然有诸多不确定性。从已有的史料看,现在能找到陶行知与杜威交往的起点或许不是在课堂上,因为杜威在哲学系任教,陶行知进的是教育学院,可能是直接在哲学系受教于杜威的同乡胡适将陶行知引荐给了杜威,因为胡适到哥伦比亚大学是“专治哲学,中西兼治”“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1]而奔着杜威来的;或者是直接给陶行知授课的杜威好友孟禄(Paul Monroe)的引荐。196月16日,胡适的日记里夹了一张标明陶行知为杜威和安庆人胡天濬拍的合影照片,胡适还附有两行文字:“杜威(Joho-Dowey)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其学说之影响及全国之教育心理美术诸方面甚大,今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部长。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学焉。”[2]从胡适的表述可以判定陶行知修过杜威的课,现有的资料看不出当年陶行知直接修了杜威的什么课,单中惠直接说:陶行知“选听了杜威开设的一门‘学校与社会’课程”[3],陶行知听这门课当是跨学院的选修。可以确定当时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有多次直接交往。
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对杜威为主将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实验主义教育方法是有高度认同的,这成为他得悉杜威到日本就产生要请他到中国讲学的动因。这一动因的第一倾诉对象依然是胡适。
193月12日,陶行知写了第一封给胡适的信道:“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我觉得又惊又喜。”他惊的是“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喜的是“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4]于是相约南北统一起来,写信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决定由郭秉文去日本的时候当面邀请。作为杜威来华的预热,胡适为《新中国杂志》向陶行知约稿写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该文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为题发表于3月31日《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
193月31日,陶行知再次给胡适写信,说接到郭秉文从日本的来信,“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意留中国一年”[5]。他们商讨如何安排好这一年的接待,后决定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194月30日午后,杜威与夫人阿丽丝和女儿罗茜抵上海,“码头欢迎的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表陶知行、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6],杜威一家被安置在沧州别墅。5月1日,陶行知、胡适陪杜威夫妇参观《申报》馆。
195月3日,杜威到中国的第一场报告由江苏省教育会举办,讲题为《用平民主义做教育的目的,用实验主义做教育的方法》(一说《平民主义的教育》),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报告由黄炎培主持,陶行知组织,蒋梦麟翻译,毛泽东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听众,对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7]。演讲前主办方分发由陶行知撰写的《杜威先生小史》。
此后,5月18日下午7时,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真正之爱国》,陶行知担任现场翻译[8]。5月25日晚,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共和国之精神》,陶行知担任现场翻译,各校学生听讲者3000余人[9]。5月底杜威离开南京,前往北京、天津演讲,由胡适等负责接待、翻译等事宜。6月24日,陶行知致信胡适,告诉留杜威在华一年的计划,“南京、上海方面准备合筹款4000元”[10]。此后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工作。
194月6日起,杜威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哲学十讲(宁)、哲学史十讲、试验的论理学三讲,由陶行知主持并翻译,历时3个月。
杜威在各地讲演由记录员把全篇讲词录下来送给日报和杂志发表,共有58篇,后来结集出版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发行。这次讲学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19适应儿童个性发展的新学制确立,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深刻且久远。
197月,陶行知、胡适欢送杜威回国。胡适在杜威回美国的时候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11]
陶行知办晓庄学校的情况杜威知道多少,缺少可信的资料。1929年10月15日,设计教学法发明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到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参观,并拍摄影片带回美国。在晓庄学校的演讲中,克伯屈充分肯定了晓庄实验,并承诺:“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中国的晓庄有一个的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12]他是否回去向杜威介绍了陶行知的情况,没有资料证据。从未有确证的不少人传说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称赞“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①的说法推想,杜威当时知道陶行知在晓庄的办学情况。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后,杜威联合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等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说明杜威在关注陶行知。
1936年11月22日凌晨,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在上海被逮捕,发生了“七君子之狱”事件。陶行知身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也在同一道通缉令中遭到第二次通缉,仅因身在国外未被捕。他在美国得悉这一事件便请求杜威、爱因斯坦、甘地等发电给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要求释放救国人士[13]。12月1-10日,陶行知到哥伦比亚大学先后看望了孟禄、杜威和克伯屈三位教授。12月21日,在陶行知推动下,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决由英国国会议员贝克先生领衔发电报给南京中央政府:“我们对于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委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史良及其他和平运动者之被捕深感痛心,我们出于保障世界和平之诚意,希望释放他们。”[14]1937年2月初,杜威、爱因斯坦、孟禄等16人致电蒋介石,表示对“七君子”事件严重关切[15]。
陶行知在美国的活动得到杜威等人的大力支持。1937年2月11日,陶行知给在吴树琴的信中说:“我现在决定在美国再住六个月,承杜威先生介绍,将到各地去演讲,随时还回到纽约来。”[16]
1937年12月4日,陶行知拜访杜威,这次他是为联名抗日而来。在征得杜威同意后,12月6日,陶行知草拟了“杜威宣言”,将所拟宣言及电稿发电给甘地、罗素、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四位先生,征求联名。13日,他们(甘地22日来电参加)共同发表宣言:“鉴于东方文明正遭恣意摧毁,为着人类、和平与民主,我们提议各国人民组织自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将战争物资出售和租借给日本,在有助于其侵略政策之各方面停止与日本合作,同时尽可能给予中国各种援助以进行救济和自卫,直至日本自中国撤退其一切武装力量并放弃其侵略政策为止。”[17]14日,陶行知将宣言在全国播音台广播并送通讯社的消息写信告诉生活书店的邹韬奋[18]。23日,陶行知再访杜威。27日,他参加了杜威的家宴[19]。
或许因为战争,陶行知回国后在重庆办育才学校,连吃饭的保障都困难,此后杜威与陶行知之间的话题聚焦到民主建设。1944年6月10日,杜威从朱启贤处了解陶行知的情况后给陶行知写了封亲笔信:“很高兴你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还在继续你的教育工作。美国正在为你们遭难的国家尽一点力,这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我期待着,我想你也在同样地期待着有一天,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而是在带根本性的各方面,帮助你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教育,做比过去多得多的事。这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民主的目标和方法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建立起来,我担心民主体制也不可能在美国一个国家盛行不衰。”[20]②
1944年9月20日,陶行知在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上做专题演讲《创造的儿童教育》,提到并引用了杜威的回信[21]。1945年11月10日,《民主星期刊》发表陶行知以《论中美两国关系》为题的致杜威博士的长信,开头几乎引了杜威回信的全文,承认民主是中国的第一需要,并说:“我向美国朋友建议,您一定同意,凡有益于中国民主的事都可以干;凡有害于中国民主的事都不可以干。”接着陶行知表示希望美国人“做中华民族的朋友,不做一党一派的朋友”,以“可惜得很”为转折,对赫尔利大使及其身后的美国政府进行了抨击,进而提出“尤其希望先生和我们中国爱好和平人士……停止美国军人参加中国内战以停止中国内战”,最后希望杜威用当年发表《杜威宣言》“同样的精神来号召:(一)停止美国过剩军火输入中国。(二)停止美国军人参加中国内战。(三)停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四)在完成日本撤军任务时,撤出美国在中国之军队”[22]。
这封信在中国公开发表后,1946年初朱启贤从美国来信告诉陶行知,杜威并未收到陶行知的这封信,并说杜威“应蒋梦麟约原定今年八月间赴华讲学,并参与中国教育改造之设计。唯现在身体欠适,届时能否成行,殊难一定”。[23]
1945年,昆明“一二·一”事件发生后,陶行知口授了一封电文给杜威:“希望通过您,通过您的国际威望和影响,伸出友谊的手来,有力地支援我们民主党派和为民主与自由献身的战士,以抵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他强调:“杜威博士!过去我曾聆听过您的教益,今天作为您的亲密朋友……希望通过您,用您的威望和影响,使美国政府制裁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迫使他接受人民的愿望,使我国实现联合政府的原则,从而走向和平民主新的未来!”[24]
杜威是否收到上述电文不得而知,但他未能实现再到中国之愿,也未见到他对陶行知上述电文的回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杜威、克伯屈和罗格三人致电陶行知治丧委员会:“今闻陶行知博士突然逝世,不胜哀悼,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25]1946年12月9日,纽约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与冯玉祥担任名誉主席,并分别发表演讲,美国教育名流300余人参会[26]。
陶行知的去世为杜威与陶行知的交往过程画上句号。
二、走出“投射效应”
“投射效应”是指认知上受自己的定位、情感与意志影响,从而难以对认知对象的真实状况及其关系做出客观、真实、准确、完整的判断。投射效应使人们倾向于在自己已有知识阈限内感知对象,而不是按照被观察对象的真实状况进行认识,从而产生远近、真假、大小等方面的偏差。对陶行知与杜威的投射效应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陶行知力邀杜威来华讲学,一直到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日常工作终止。由于杜威在美国已有很大影响,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被当作西方的圣贤、西方的孔子(特别是杜威19的60岁生日刚好是孔子的农历生日)、现代化的导师。不少人从杜威的角度看他的中国学生,看陶行知的时候贴上了杜威的标签,由此带来众多亲疏、荣辱、利害,主要作用是提高了陶行知的社会影响;陶行知的众多学生和追随者从陶行知的角度看杜威,他们通过陶行知了解杜威,又由于陶行知挡住了对杜威更为真实完整的认识,很多人就仅读陶行知介绍杜威的文章而较少读杜威的原著。
第二个阶段从晓庄学校创办到1936年。晓庄是个多元包容的学校,中共晓庄学校支部“因为陶先生从不干涉大家的政治思想,相反,对师生中好些不满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还采取放任态度,甚至做些幽默解释。因此,我们一面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一面又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这样,市委就指示我们,现在不要反对陶的改良主义,要利用晓庄的自由环境。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力量”[27]。这一时段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投射开始产生,对于陶行知学生的中共成员而言,陶行知是与资产阶级教育家杜威一脉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在晓庄以外有人认为陶行知是亲中共的“过激党”,这种投射效应源自晓庄内的中共党员,并留存很久。
第三个阶段是从1936年到1944年。由于联合救国,大家把杜威当成经由陶行知联系的、为联合救国的中国人说公道话的美国朋友。由于不同的人政治立场不同,各人都希望杜威与自己的立场接近,陶行知本人也是这样希望的。
第四个阶段是从1945年到1950年,主题转变为争取民主。陶行知在1945年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偏向,杜威难以对陶行知做出有效的回应,因为陶行知一方面要求杜威敦促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杜威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使美国政府制裁国民政府,支持自己所属政治团体以及与自己所持政治立场相同的人,事实上,此时杜威与陶行知在政治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陶行知在信中反复强调是自己朋友的杜威已经显示出对杜威不是像从前那样尊重。这样的关系和时代背景使投射效应产生叠加和多次折射而变得更为微妙、复杂。
第五阶段是从1951年到1981年。当时马克思主义或经过中国人加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中美政治的对立成为大背景。大陆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在批判胡适的时候投射到他的老师杜威,杜威也受到批判,被投射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对立面;再从杜威那里投射到陶行知,作为杜威的学生多少有些反动,与资产阶级脱不掉干系。赞成陶行知的人竭尽可能撇清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而批判陶行知的一方则强调陶行知与杜威的联系,认为陶行知和杜威都是与人民立场对立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办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第六阶段是从1981年至今。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人们开始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杜威的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思想。1981年全国政协开会为陶行知平反后,陶行知研究兴起热潮,投射效应渐淡但依然存在。其方向一是强调陶行知与杜威的不同,二是强调陶行知对杜威的超越。张文郁即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和实践远远超越了杜威,“既反对本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反对帝国主义输入的洋化教育”[28]。
在认识杜威与陶行知之间的关系上主要存在四种投射效应。第一种是从陶行知对杜威的投射。受这种投射影响的中国人最多,他们看到近处的陶行知,看不清远处的杜威。很多陶行知的研究者仅限于知道杜威是陶行知的老师,未能完整地读过一篇杜威的文章或一本书,想当然地认为陶行知比杜威更伟大、更具有人民性。
第二种是从杜威对陶行知的投射。有这种投射影响的一部分为国外学者,另一部分主要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中国学者,认为相对于杜威,陶行知在各方面都不足挂齿。
第三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陶行知与杜威的投射。这种投射有文献可查的是刘季平以“满力涛”的笔名发的文章开始,他从矛盾关系的视角批判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认为杜威通过观念上的纠正就可以将生活与教育的矛盾解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论才能将“生活”和“教育”这两个“不是装在两个器皿里的两个东西,而是真正统一的一个东西了”。[29]刘季平自以为持马克思主义批判陶行知与杜威,一直延续到1978年后才开始反思,认为自己“仍然有不少必须认真检查改正的左倾思想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我们给他扣的三顶大帽子”——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有趣的是刘季平将这一认识归结到“越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越加认识到”[30]的结果。
陶行知对马克思是有所认同的。1933年春节,他参与成立读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陶行知与蔡元培、章乃器、李公朴等学术界100余人发起纪念会。1936年10月30日,陶行知专程拜谒了马克思墓,并写诗赞颂:“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31]将陶行知投射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是由于产生投射效应者所持的已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于是陶行知强调“爱满天下”受到无阶级性的批判,“教育救国论”由于不革命受到批判,教育工作者由于未能理解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而遭到批判,陶行知的改革实验被认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科学的”。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陶门弟子方与严、戴伯韬等人在为陶行知生活教育辩护时,也不得不承认陶行知思想源自杜威的局限性[32]。投射效应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共领导中与陶行知交往较早的李维汉认为,陶行知“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33]。更有人认为陶行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34]。“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意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按照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去理解实用主义,那这两种哲学作为体现现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哲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说殊途同归。”[35]理解了这样的内在关联,才可能避免主观使用投射而遮蔽对客观存在的认知的影响。
第四种是中美关系的投射。杜威和陶行知出生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国关系的状况投射到对于两人关系的判断上也是常见的。在中美政治关系恶化的时期,“崇美”就是罪,杜威和其他西方教育家的思想在中国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杜威被指责为“进步主义面具掩盖下的狡猾敌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代言人”“中国和全世界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作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因此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改革家”,以至实用主义也因为是美国的而遭到批判。为陶行知辩白的学者争辩陶行知不同于杜威,因为杜威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而陶行知“总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上”。
投射效应下的言说都与事实存在距离,不能以民粹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扬陶抑杜”,也不能怀有崇洋心态“抑陶扬杜”,不能拿被误解的杜威与被投射的陶行知进行比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投射效应影响着对陶行知与杜威关系的理解与判断。要清晰准确地表述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必须消除各种投射效应,看清原本的杜威与原本的陶行知。
三、思想理论:原理与应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理论主要源于杜威是没有争议的,二者的内在关联如何,则有不同看法。下文将从发展过程、内容和逻辑关联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一)从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发展过程看其与杜威理论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19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而实际的情况是陶行知在回国后若干年实践后才提出有别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其发展的时间节点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197月陶行知送别杜威回国前,属于沿用杜威理论与概念阶段。这一阶段陶行知文章中提及杜威的频率最高,基本是原文照引。19陶行知所写《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发表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会刊》第1期,在194月《金陵光》学报第9卷第4期和192月《新教育》第1卷第1期上再发表,主张“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列数培根(Bacon)、笛卡儿(Descartes),认为“杜威之集成教育哲学,以试验”[36]。
在此期间,陶行知仅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非正面引用杜威:“美国人士视职业教育与学赚钱(Learning to earn)为一途,有识者如杜威(Dewey)先生辈,咸以其近于自私,尝为词以辟之。”[37]其余均以推崇的语气引介杜威:“古今名人莫不由研究教育而出。如达尔文、杜威、威尔诺刻等”[38],“吾尤愿诸君为白斯达罗齐,为福禄伯,为条魏(杜威),为曹朗达”[39]。陶行知在杜威来华之前写《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并坚定地说:“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40]他在介绍杜威的十六种著作之后认为:“和教育最有关系的,一是《平民主义的教育》(通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二是《将来的学校》(通译:明日之学校),三是《思维术》(通译:我们如何思维),四是《试验的论理学》(通译:伦理学)。这四部书,是教育界人人都应当购备的。”[41]
194月,陶行知撰文《试验教育的实施》,强调:“最好是把杜威的思想分析拿来运用。按照杜威先生的意思:第一,要使学生对于一个问题处在疑难的地位;第二,要使他审查所遇见的究竟是什么疑难;第三,要使他想办法解决,使他想出种种可以解决这疑难的方法;第四,要使他推测各种解决方法的效果;第五,要使他将那最有成效的方法试用出去;第六,要使他审查试用的效果,究竟能否解决这个疑难;第七,要使他印证,使他看这试用的法子,是否屡试屡验的。……有了这个方法,再加些应有的设备,必能养成学生一种试验的精神。”[42]197月,他在阐述《新教育》时说:“‘教育’是什么东西?照杜威先生说,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43]在这一阶段,他显现出对杜威的笃信不疑。
第二阶段为“活的教育”提出阶段。19送走杜威后迎来孟禄,陶行知陪同孟禄在各地做调查的过程中获得对中国教育现实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接着出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更深入地接触教育实际。19,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暑期学校做了题为《活的教育》的讲座,后来在清华学校等地做过同题讲座[44],较大程度上展现了有别于杜威的思考。19,陶行知几乎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运动,他参与这一运动的思想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杜威,但推进中遇到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实际中的,这给陶行知创造了将杜威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更多地思考而非简单套用。191月初,陶行知在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会上演讲《教育与科学方法》,倡导在教育上应用科学方法,反对简单用古人或外国人的方法,介绍了杜威思想分析的五步方法:第一步要觉得有困难;第二步要晓得困难的所在,就是要找出困难之点来;第三步是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第四步是在这种种方法中选择一种;第五步是必须通过实验验证。他认为通过这五步功夫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强调使用这些方法时要求是客观的、量化的,在教育研究中要重视组织、教材和工具,主要的工具是统计和测量。他指出:“每人都存用科学方法去办教育的决心,每人都去研究或解决一个小问题,我敢说,不出三十年中国教育准有好的成效。”[45]他所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将推进科学教育作为重要议案,显示出对杜威理论更灵活的运用。
第三阶段为提出“教学做合一”阶段。1925年底,陶行知应邀到南开讲座,张伯苓听完他的讲座后问:“您的理论是做学教合一吗?”陶行知由此得到启示,提出“教学做合一”,此时有独特体系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才有了内核。1929年5月19日,陶行知在晓庄寅会演讲《生活即教育》,他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翻了半个筋斗。实行‘教学做合一’的地方,再也不说‘教育即生活’……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46]“教学做合一”的提出是由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转折点,此后通过晓庄学校的乡村教育实践,丰富完善成为独具特点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第四阶段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完善阶段。晓庄学校被封闭后,陶行知仍通过普及教育(1931)、国难教育(1934)、战时教育(1938)、民主教育(1945)等运动丰富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1931年底,陶行知在短文《思想的母亲》中再次提到杜威的五步思想法,除了重述原文,提出“行动是思想的母亲,科学是从把戏中玩出来的”新命题,他认定杜威“这反省的思想之过程便是科学思想之过程”的同时,指出:“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47]这段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杜威的表述,整体看还是运用,在运用中遇到问题的修正。从逻辑上说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如同先有鸡或先有蛋的关系,也算不得理论发明。
在陶行知理论和实践后面的各个阶段,都有杜威的因素存在。直到陶行知去世前极力争取民主,实施民主教育,依然是与杜威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相伴随着发展,并通过信函沟通显现出高度一致。
(二)从内容上全方位分析两人的思想与理论关系
1.杜威在思想容量和思想深度上远超陶行知
对思想容量不需要做太多的论证,只需要将二人留下著作做个简略的比较便能看出。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为收文最全的陶行知著作集,共12卷,不到一千万字,其中还包括日记、诗歌等;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的《杜威全集》共37卷加上1卷索引,共3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文字量是《陶行知全集》的三倍多,内容覆盖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比较二人的“全集”目录即可看出,杜威的思想理论结构和范围远比陶行知宽广宏大。杜威的教育著作已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相比而言,各国也有一些陶行知研究者,但陶行知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远不及杜威。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
杜威与胡适是偏向理论思索型的人,陶行知和克伯屈是偏向实践操作型的人。陶行知认为在杜威的反省五步中,“要在‘感觉困难’上边添一步:‘行动’”[48],也反映了这种差异。杜威一生办过学校,但更勤于或擅于思索,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著述宏富;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家中也算著述宏丰,若任意挑选两人的文章对比,便可看出杜威的思想深度、逻辑性、哲理性远超过陶行知。陶行知论述生活教育的几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杜威理论具体化、实践化的进一步探索;或者说是中美两国处在不同的社会与教育发展阶段,陶行知非常清楚中国与美国的社会与教育现状的巨大差异,陶行知与杜威面对的问题不同,需要面对现实进行不同的求解。陶行知的文章、诗歌与实际行为的相关性高于杜威,哲理性则明显低于杜威;杜威关注实践,对实践的思考提升则明显高于陶行知。就批判性而言,杜威对西方原有哲学与教育的批判比陶行知对包括杜威在内的前人教育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广泛,由此影响到整个西方哲学界。
2.从方向上看两人的思想是同向的
“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49],陶行知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陶行知多次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我们也用得很多而且很熟的,就是‘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of life)。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John Dewey)先生那里来的,我们在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50]“与‘生活即教育’有联带关系的就是‘学校即社会’。‘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他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51]
对于为何要做这种改变,陶行知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52]这种改变本身不是理论根基的改变,而是依据实际案例做出的方式方法的调整。
陶行知在分析“杜威在美国为什么要主张教育即生活”时说:“我最近见着他的著作,他从俄国回来,他的主张又变了,已经不是教育即生活了。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是零零碎碎的实验,有好多教育家想达到的目的不能达到,想实现的不能实现。然而在俄国已经有人达到了,实现了。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53]陶行知当时看了杜威的哪篇文章哪本书无从查考,这段话的整体逻辑和事实都存在难以经得住推敲之处,但它显示陶行知将杜威的理论做了修改后方向没有改变的基本判定,而且以他与克伯屈的对话证实杜威的变化与陶行知的变化是同步的。
“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的重心都在生活,“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的重心都在社会。学校与社会密切相连是其共同信念,都是要向生活回归,重视发挥社会的教育作用,而不是颠覆,没有改换方向的含义。把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把教育普及到生活所包含的领域,也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三)杜威与陶行知之间是原理与应用的关系
1.整体看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对杜威教育原理的应用
陶行知在给《1924年世界教育年鉴》撰文中写道:“自19以来,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孟禄(Paul Monroe)、杜里舒(Von Driesch)、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演讲以及与我国知识界领袖和学生的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特别提一下杜威和孟禄博士的来访,因为他们的访问对中国教育的改造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之外,杜威博士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已经成为我国初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之一。自从他访问我国以来,在初等教育中已经进行了若干实验。他的哲学促使教育系的几个学生为实现他的哲学而设计了若干技能和方法。孟禄博士强调,教育是一种应用,而不是观念的获得。他的劝告是以19的仔细调查为根据的,所以引起了对各种教育问题的认真思考,尤其促进了中等教育和科学教学的改革。”[54]这段陈述说明陶行知将当时中国受杜威影响的教育活动定位在对杜威理论的实际运用。
1929年1月15日,陶行知在欢迎自己的老师克伯屈的致辞中说:“杜威先生的教育哲学,是世界上公认的,而根据这个理论找出具体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理论,予教育界一个伟大的贡献的,就是克伯屈先生发明的设计法。”[55]陶行知对克伯屈的称道显现出他对为杜威的理论找出具体方法的工作重要性之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陶行知与克伯屈相对于杜威近似的定位,即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将杜威的理论原理运用于实践。陶行知的另一段陈述也显示出他所追求的是将杜威的哲理加以运用:“自杜威来华讲学,生活教育之名,已成中国教育界之口头禅。但只有生活教育之哲理,而于实现此哲学之具体方法,未加注意,故生活自生活,教育自教育,渺不相关。”[56]其下文就是讲他的理解与运用。
2.陶行知在运用杜威教育原理中创立了新的案例
杜威哲学的主要特征在于他聚焦生活、行为、实验、实践、探究,陶行知在认识论上认为行以求知知更行;在本体论上坚持以人为本,教育满足生活向前向上发展的需要;在价值论上主张人民第一,民主、自由、创造。这些都在杜威的思想理论范围之内,陶行知结合中国实际,用中国的语言做了更为生动、易于接受的表达。不少人举出陶行知变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为例,说明陶行知超越了杜威。如果孤立地看这几句话,陶行知的表述确实更合理,也显示两种表述有巨大差别;如果更大量阅读杜威和陶行知的著作,就能发现杜威的思想并未定格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在那里,陶行知也没有实现对杜威的超越。但陶行知确实对自己所遇到的实践有所创新,创立了不少运用生活教育理论的创新案例,创建出相对系统、有别于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是杜威的中国学生中创建最多的人。
3.陶行知与杜威之间不存在阶段性的差异
整体看陶行知思想的源流与轮廓,它的来源主要为两大类: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墨融合,其中主要受孔子、墨子、王阳明、朱熹、戴震等人思想的影响;二是受卢梭、裴斯泰洛齐、杜威等人的思想影响,其中杜威的影响更为深刻直接。在受杜威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来融入其思想的中国传统思想参与其中形成新的组合,另一方面结合他遇到的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独特的加工改造。陶行知曾说:“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我们现在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在此问题上,一面实行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我们认定必须这样,将来中国的新教育才能产生呢!”[57]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生活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有敏锐的领会能力,但他在这方面容纳的素材没有陶行知多。杜威理解问题接近生活又偏于哲理,陶行知立足生活又乐观诗意。所以陶行知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运用杜威的思想理论,又不像某些人认为的两者本质上不同、主义不同、服务阶级不同。陶行知对杜威的论述有批判、有创造,杜威对自己的过往论述也有批判和新创,这两者性质是相同的,方式也类似;但就两人已有的著作而言,陶行知并未超越杜威进入一个新阶段,两者之间不存在阶段性的差异。
当作出杜威与陶行知的思想之间是原理和运用关系的判断时,两者不存在高低,在教育与社会改进中都是必要的,两者配合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四、事业和人际:激励与支持
论及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必然包括在事业上的建树。首先,杜威在陶行知的事业中一直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
他在陶行知早年身份与使命确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陶行知19回国直至1946年去世,将他的生命中主要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最初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和行政人员。杜威和孟禄的访华以及陶行知的伴随,一是帮助陶行知认识了中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引发他做了根本性的自我改造,重新确定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身份和使命,离开大学教授的职位转而到中华教育改进社从事中华教育改进事业,抛弃了归国学者常有的表面化的西方印记;二是把陶行知带进了20世纪代初由杜威与孟禄等人促成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为主导的中国教育与现代化运动的中流,为陶行知后来的事业发展准备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三是杜威的到来为陶行知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融入社会高层提供了契机;四是陪同杜威和孟禄到各地演讲与调查,为陶行知提供了依据现实、灵活理解和运用杜威理论的现场见习。简而言之,如果说19是陶行知师从杜威、接受其理论的起点,19后是他师从杜威走上事业的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上,杜威竭尽所能给予支持,19陶行知在南高师创办暑期学校开展教师培训,“开始试办男女同校,杜威夫人冒暑留在南京,襄助指示一切”[58]。
19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192月确定聘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开始仅聘请成立时在场捐金洋4000元的孟禄等5人为名誉董事[59],事后确认杜威也列入,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骞、张一麟、李石曾7人为名誉董事[60],也显示出杜威对陶行知的支持。此后,依据杜威推荐,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名义,邀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推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麦柯尔等人就理科教学、教育测量等专题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和指导。
陶行知自始至终将杜威作为对自己事业的激励和民主社会建设的引路人,创办乡村教育时提出《我们的信条》等做法能看出是他对杜威的模仿。1937年,陶行知总结自己的乡村教育十年时特别强调:“生活教育已引起华侨和各国的认识。他们大家对于这个生活教育和乡村教育,是非常的注意。今年世界新教育同志会开会的时候,已经把生活教育报告给大家,大家都感觉到很大的兴趣”,“就是美国的杜威先生和孟禄先生对我们的办法非常赞成。”[61]
其次,陶行知与杜威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关系。陶行知去世时,曾经的亲密朋友胡适、张伯苓以若无其事态度应对,杜威不仅发来唁电,而且在美国参加陶行知的追悼会。从陶行知的感受看,他与杜威之间的交往在记忆中总是愉快的,1927年底他正为晓庄学校忙得不可开交时,冯玉祥希望他到河南筹划河南的教育,行前与晓庄同人签下返回时间的约定,途中写信给晓庄的同志道:“这晚住天成栈,仿佛那年杜威先生游泰山时所住的小客栈一样的有趣。”[62]一句不经意的话显出陶行知对杜威的感情。同样,杜威对陶行知安危的关切、1944年写信对陶行知艰难办育才学校的嘉许与鼓励,都是这种情感的体现。在这种情感基础上对杜威与陶行知分阶级、论革命、比高低,显然有违二人原本的意愿。
再者,陶行知对杜威的思想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威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由于杜威在中国访问和讲学两年多(从194月30日至198月2日)直接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陶行知、胡适等人的推崇和宣传的结果。陶行知除了自己宣传杜威,还支持别人的宣传工作。196月24日,应邹恩润(即邹韬奋)之请,陶行知校阅他所翻译的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并对部分作了改译,介绍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
19陶行知全身心推行平民教育,是对杜威思想的独立施行。19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上介绍:“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作教育的目的,试验主义作教育的方法。”1910月,杜威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该校师生联合组成平民教育社,创办社刊《平民教育》,认为教育的改良是一切社会改良的根本,提出平民教育就是“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与平等思想的教育”,陶行知的做法是杜威思想的继续实施。
总而言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源于杜威关于学校和社会、教育和生活以及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这是基本事实;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也是基本事实。中美教育交流需要像陶行知和杜威之间发展的那种真诚的友谊和信赖,消除各种投射效应,解除对杜威的隔膜,是深化陶行知研究的需求,也是中国教育开放吸纳人类优秀思想资源、实现现代化和推动文明进步的现实需求。
注释:
①这一说法被很多文章引用,却找不到一个经得起推敲的依据。
②此处引用的是根据杜威英文信的重译文。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2卷[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21.
[2]胡适.胡适作品集37·胡适留学日记(四)[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36.
[3]单中惠.传承与创造——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J].中国德育,(14):24-28.
[4][5][10][16][18][6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216,218,422,453,185.
[6]本埠新闻[N].申报,1919-05-01.
[7]凌文.毛泽东与陶行知的第一次见面在上海之考证[J].党史文汇,(6):60-62.
[8]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19-05-26/27.
[9]南京快信[N].申报,1919-05-26.
[11]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J].东方杂志,1921,18(13):121.
[12][46][47][50][51][52][53][55][56][57]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70,7-8,139、667,489,491,491,491-492,467,595,356.
[13][15][19]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795,796,799-800.
[14]陶行知.世界和平理事会营救中国七领袖[N].大众日报,1937-03-19.
[17][5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6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628,321-322.
[20][22][23][2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782,777-781,783,784-785.
[21][6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44,211.
[25]新华日报,1946-10-08.
[26]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654-656.
[27]刘季平.中共晓庄支部与南京市委工作正反经验一例——关于1928-1930年南京地下工作的一些情况[A].刘季平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426-427.
[28]张文郁.陶行知传略[J].晋阳学刊,1981(5):80-89.
[29]满力涛.教育与生活[J].生活教育,1935(2):19.
[30]刘季平.正确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A].刘季平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309-310.
[3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7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672.
[32]方与严.再认识陶行知先生教育学说并批判自己[J].人民教育,1952(7):25-29.
[33]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0.
[34]胡国枢.论陶行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J].浙江社会科学,1992(1):61-65.
[35][49]刘放桐.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15-23.
[36][37][38][39][40][41][42][43][44][45][5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9,13,260,272,300,302,310,312,404-410,516-523,347.
[4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26.
[59]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纪录[A].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562.